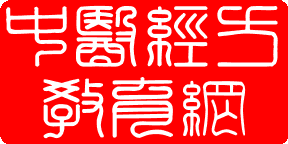在危急時刻,有時有技術比沒技術糟糕
年輕時認為“淹死會水的”這個論斷不能成立,因為不合乎邏輯。真要是會水怎麼會被淹死?既然被淹死了又怎麼能稱得上是會水?於是,凡是被淹死的,我就否定其游泳技術。我認為這個邏輯像鐵三角一樣牢不可破。可後來我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好多泳者正是死於有比較好的游泳技術,如果不堅持其游泳技術不至於送命。從而驗證了“淹死會水的”這一說法。
我研究有人拍的游泳者淹死過程的照片。通過分析,我認為有的泳者技術相當好,姿勢沒問題,力度也很強,之所以淹死,問題不是出在技術上而是出在游泳觀念上,他們自始至終不肯放棄技術依賴。最讓人痛心的是,即使是救人的英雄到最後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游泳觀念有問題,如果他們在最後一刻改變認識就都能完成自救,他們成了自己思想認識的犧牲品。
長期以來,人們憑藉技術走到自然的對立面。技術成為人們戰勝自然、征服自然的武器。我們不僅形成技術依賴,還形成了技術思維定式。那就是依賴技術而不是依賴自己。這就造成了在危急時刻,有時有技術比沒技術糟糕的情況。靠技術游泳,尤其以競技狀態渡江是很魯莽的做法。如果泳者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能意識到人的技術和體力是有限的,能收斂技術或乾脆放棄游泳技術,順應水性,不與風浪搏擊,把自己當成水的組成部分,你就會發現水並不是與你敵對的,不是想置你於死地的。當你不是拼命地想要掌控身體的主動權時,你會發現你並沒有失去這一主動權。
那麼多的泳者不是死於游泳技術不佳而是死於不放棄游泳技術的思想觀念,這是一件多麼令人痛心的事情。讓一個技術高超的人在關鍵時刻能丟棄技術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味拼搏,到最後也不另辟道路是大多數人的做法。有誰認識到靠技術過江是個危險的思維定勢?
有一個四十多歲的老賊在牢裏傷心地對我說:“我真不應該在這裏,我已經發誓再也不偷了,可是,唉,我知道你不會相信我。”我說我理解他,他兒子長大了,他是真的不想讓兒子瞧不起他,可他沒有辦法處理他身懷的“絕技”,無法改變技術依賴的心理定式。我說,除非砍掉右手,否則他不可能不偷。
看毛澤東暢遊長江的錄影,我頗吃驚。他老人家沒有泳姿,他游泳就是在水裏翻滾,無技術可言,從這一點上可以說他不會游泳,我懷疑毛主席要是渡江的話速度一定很慢。但我得承認毛主席識水性。他為什麼號召人們到江、河、湖、海裏去游泳,到大風大浪中去鍛煉?因為在游泳池裏沒有多少水性可識。在游泳池中學到的游泳技術很可能讓人送命。
學游泳,技術不是一切,有很多東西是在技術之外,不知道這一點,就算是會游泳,但不能算是識水性,而不識水性就有送命的危險。
中醫有時候看上去是那樣地缺少技術含量,是那樣地無技可用、無技可依,即使有技,這個技也是藏在自然的狀態之中,那樣地不顯、不露,這在科技時代真是有點讓幹中醫這行的人蒙羞。可是,正像一個走進原始森林的現代人,他的信心和勇氣不是來自於內心,而是來自於他手中的槍。一旦失去這支槍,一旦子彈打光,他就失去所有的價值。西醫將人的所有價值都外化了,從內在上看不到人。中醫看上去落後,可是我們是不是也應看到中醫在技術與醫學關係的統一上確有獨到之處呢?
母親沒有教給我技術,沒有傳給我絕招,迫使我無技術可依,只能向內挖掘,這時,你很可能發現,你想外求的東西內在已經具有。如果一個人把握了內在的具有後再獲取技術,技術才真正是為人所用,而不是人去做技術的奴隸,甚至被技術所害。
我對一群孩子說,水對人本是親善的,托扶你的,而人本來天生就會浮水的……我讓一個孩子閉上眼睛,把他托放在水面上,然後抽出手,對其他孩子說:瞧,我們還用學游泳嗎?我們本來是可以浮在水裏的。躺著的孩子睜開眼,見我手在上,他身子沒敢動,可已直線下沉,我一手拎起他道:看,只要我們心裏不自信,這水就不再托扶你。
如今的醫院離不開設備,醫生離不開儀器,醫院和醫生共同組成一個嚴密的大機器。醫務人員的身心緊緊依附著技術、依附著醫院,離開醫院,醫生就什麼也不是。他們不是個體的人、健全的人和完整的人,談不上心靈的自由和解放……大學生們為什麼往大城市擠?為什麼到大城市求職?因為學校給予他們的書本“技術”就像賣身契一樣,將他們依附在具有機器性質的社會技術團體中了。
這種依附關係是如此折磨人,以至人們的心理普遍不適,產生種種心理問題。對此,人們多從社會角度進行分析,少有從科技角度著眼;所找的多是單一原因,少有複合因素。出於技術觀念,有病就得治,不治就是錯誤,不具有技術含量的治、不治而愈的醫就要受到指責、嘲笑。社會進步的標誌表現在治病上就是有病必治、小病大治、大病動用全院、甚至全國的醫療手段治。想要滿足人們這一欲望,我們的錢再多十倍也不夠,因為我們窮的是心。
被淹死的會水者至死不明白自己的死因,活著的人以一句簡單的“技術不高”就把責任還給了死者。正如北京大學用“抑鬱症”一詞就把大學生的死因還給了死者,使這所當年盛產瘋狂天才的學校淘汰了瘋狂,也淘汰了天才。“淹死會水的”是一句什麼樣的咒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