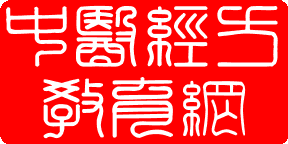女兒的師傅診脈很有意思。他給人摸脈,把在一旁看的我給逗樂了
女兒的師傅診脈很有意思,他給人摸脈,把在一旁看的我給逗樂了。他對病人說:“你有膽囊炎、腎結石、子宮肌瘤、高血壓……”病人不信,他就開檢驗單,讓病人查。全都一一驗證。
真沒想到,中醫會這般發展。是呀,作為考官,如今許多病人來看中醫時不是心懷答案,而是手拿標準答案———西醫的檢驗單。對此,我並不為中醫叫屈,因為中醫在歷史上一直是在不斷檢驗下生存和發展的。
女兒的師傅也用西醫精確的量化指標時時與脈象、藥量、藥性做衡量對比,這使他比以往的中醫人與西醫有更多的結合點,對中醫的診脈、開藥時時加以修正。
中醫就是在不斷的校對、驗證、修正中建立起來的,所以,又信西醫又信中醫在老百姓身上是一點不矛盾,中國人既上西醫院檢查,又找中醫診脈的局面看似有病亂投醫,其實並不盲目。大量的西醫檢驗單為中醫的診斷提供了參數,對這些檢驗單的二次利用是不是提高效率?是不是有利於中西醫結合?
中醫的整體思維就是把所有能考慮進去的因素全部加以考慮,當然也包括西醫手段。
一位香港中醫治療肝腹水,他知道按中醫的理論該用瀉法,但中醫書上又不讓對危重病人用瀉法,因為瀉傷津,病人受不了。這位中醫大膽採用瀉法,一瀉再瀉,將一個個病人治好了。他說,我不怕傷津,我給病人掛吊瓶、輸液、補血,解決了古代中醫解決不了的傷津難題。
西醫用放、化療治癌症,病人受不了放、化療的副作用,中醫給予輔助性治療,使病人能夠完成西醫的療程。
母親有時面對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補不得、瀉不得的病症時,她的心情是比較矛盾的。這樣的病著實說不破不立,或使其歸實,或歸虛,然後再重新調整。但這種治法在現代往往不被理解和接受。小時看母親給病人開過藥後,有時告訴病人,這付藥下去後,病情會加重。我對此感到不理解,誰肯讓自己的病情加重,醫生怎麼要把病人治重呢?母親也有這一顧慮,所以,有時她會動員病人到西醫那裏去治一下,借西醫之手為難解之病打開一個缺口,等病人回來後,母親再一展身手,力挽狂瀾,把病人治好。
當有的病形成痼疾,造成五行失衡、偏枯,非一般藥能解時,西醫的干預正如大毒,改變一下五行膠滯的狀態,給中醫一個再創平衡的機會,這又有何不可呢?
母親研究西藥,她還把西藥弄來嘗,像李時珍一樣,根據西藥使用後病人的反應來分寒熱五味。比如,她認為青黴素性寒,表證的用上往往就變成裏證,雖然把炎症消了,但陽氣受抑制,對已接受西醫治療的病人,她總是把西醫的治療也納入總體思考。我親眼見母親將中藥與西藥配伍著服用。
我們這裏有一個長於治小兒病症的中醫,他看西醫診所掙大錢而眼紅,便開了一家西醫門診。讓我覺得可樂的是,同樣是西藥,他用的效果就比一般西醫效果好,到他這來的患者特別多。先前我還為他轉型成了西醫而遺憾,後來看到他治病的立體打法,算得上是中式思維結合西式武器。
女兒的一個同學,跟一個很有名氣的中醫實習。他驚訝地發現,這個中醫還十分擅長用西藥,其治療效果要高出一般的西醫,也就是說,做一名西醫他也是高水準的,可他仍立足于中醫。
與西醫要攻陷中醫相反,中醫從不排斥其他醫療手段,中醫不具有戰鬥狀態,只是容納、吸收和包涵。
女兒認為,西醫的發展對中醫是個促進,一個沒有對手的武士是難以保持活力的。我也感覺到中醫在女兒這產生了變化。女兒診脈直接說西醫的病名,說出西醫的檢測指標來。這又是女兒在西醫院學習的成績。在西醫院,她借查脈搏而診脈,她借寫病歷而分析各種指標和資料,而這些分析又被她融進中醫中,這使她與病人交流時更方便、快捷。
中西醫結合的問題在於人的大腦可能還不適應東西方思維的切換。
有人說中國傳統思維是僵化思維應該剷除。我覺得剷除中式思維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是人的大腦具有的思維方式,只能壓制一時,不可能剷除。如真能剷除,對大腦來說也是損失。我認為中西醫之爭與其說是東西方文化的衝突,不如說是對人類大腦進化的一次挑戰,從猿到人,人的大腦進行了好幾次類似這樣的進化。中西醫真是水火不相容嗎?意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真就不能統一嗎?人的大腦發展到了極限了嗎?
我想,用中國思維思考以上問題,考慮如何達到水火相濟,達到中西方文化的和諧,推進人類的大腦進化,比剷除一個保留另一個要明智得多,因為中國思維理解的沖克關係不是絕對的鬥爭和你死我活的關係,而是有如火對金的鍛造,金對木的製造。中西方文化的衝突很可能將我們“沖”起,給我們創造一個建立大文化的契機。在新的大文化中,中西醫的結合將得以實現。
女兒也認識到,作為一個現代醫生,西醫臨床是必須拿得起來的。我說,你不能當一個病人需要你搶救時,你說你是中醫,無法給予緊急處置。你也不能因為離開醫院和醫院的設備就無法對病人進行救治。更不能以這是兩種思維為藉口拒絕對病人進行中西醫結合治療。我說,中西醫結合百餘年的失敗之路並不說明此路不通,中國文化能不能殺出一條生路來,我把希望寄託在中醫這裏了。醫生這個概念在今天會被賦予新的內涵。
(19)女兒的師傅診脈很有意思。他給人摸脈,把在一旁看的我給逗樂了
1 篇文章
• 第 1 頁 (共 1 頁)
1 篇文章
• 第 1 頁 (共 1 頁)
誰在線上
正在瀏覽這個版面的使用者:沒有註冊會員 和 2 位訪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