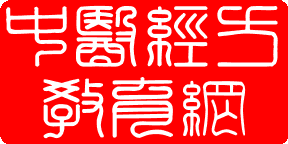母親一臉茫然,她反復自言自語:“這糟粕不是糟粕?”
母親畢竟置身于科學時代,不可能不受現代科學的影響。對中醫,她按“吸取其精華,剔除其糟粕”的新中國中醫方針,把她師傅傳給她的東西按她能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分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
有一次,一個晚期癌症病人被她丈夫背到母親這來了,母親當然治不了,可這丈夫不肯接受妻子不治的現實,苦苦哀求母親,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無奈,母親給他開了一個古方,說是給病人吃老母豬肉。
這個男人從農村買來一頭已喪失生育能力的老母豬,殺了給妻子吃肉。這女人十分想活,加之對母親的迷信,就努力地吃。到了醫生宣判的死期,她沒死。一頭豬吃完了,一個冬天過去了,女人的病竟好了!兩口子來謝母親時,母親一臉茫然,她反復自言自語:“這糟粕不是糟粕?”
一位火車爐前工,由於生活不規律,得了很嚴重的胃病。由於帶病堅持工作,吃藥的效果也不好。母親笑說,有一個“糟粕”方子治這病,說是備七口大缸,將稻草燒灰,填滿大缸,用水浸泡,浸出物會有白色物質沉澱缸底,收集這七口大缸,可得一碗。將這一碗白色沉澱物服下,可治此病。
聽了這個方子,我和魯迅對中醫的看法再一次統一,覺得中醫有療效的方子也是從這些五花八門的方子中歪打正著地碰出來的。
有一次,這個爐前工在外地發病,疼得死去活來,遇到一個老太太將小蘇打調和了一碗讓他吃下,他吃驚於怎麼可以服用這麼大劑量的小蘇打?但疼極了,老太太又一個勁地鼓動他,他就吃了,結果就不疼了。又吃了兩次,竟全好了,再沒犯過。母親聽了,就念念不忘老要泡七缸稻草灰看看那白色物質是什麼東西。
我家的一個鄰居是火車司機,剛40出頭就得了很嚴重的哮喘。那時的火車司機總要探頭看前面的信號燈,巨大的冷風灌得他根本受不了,只能在家休息。母親給他治,告訴他要養,他這輩子不能再開火車了。有一次聊天時,說到中醫的“吃啥補啥”,說人的肺功能弱可以用動物肺補,而在動物中肺功能強的非狗莫屬,因為狗不出汗,狂奔後看它劇烈喘息就可知它的肺工作量很大。這個火車司機聽了就與打狗隊聯繫,要狗肺子吃。幾十個狗肺子吃過之後,他重返工作崗位,又開上了火車,在冷風中一再探頭,也沒犯病。這令母親十分驚異。母親的驚異加深了我的印象。多年後,女兒的叔叔得了哮喘,一犯病得搶救,衣袋裏裝著激素,喘不上來氣就得噴霧。我向狗肉館要狗肺子,一天一隻給他送,他就白水煮了吃。他病好了,我從未與他探討過狗肺子到底起多大作用。
我想,隨著母親年齡的增長,臨床經驗的豐富,她對“糟粕”的否定漸漸產生了動搖。我從母親的學習過程中看到,人的學習也是分階段的,不能從人的學習內容判斷人的學習正確與否,決定學習效果的還有方式。年輕人學習時常輕易斷言優劣、對錯,造成學習上的留一半、扔一半現象,使學習走偏。上了年紀後,多觀察少判斷,結果從“愚昧”和“糟粕”中得到的啟示往往要大於正統學術。由此可知,“愚昧”和“糟粕”不是沒有價值,唯有上了年紀的人才能從中吸取營養,所以,對不理解的東西先行保全比徹底剷除要好。
有一個人找我母親看病,他的病在西醫做了全面檢查,沒查出問題。但他就是有氣無力,無精打采的。母親說他受了瘴氣,不好治。我聽了和病人一起感到奇怪,什麼是瘴氣,怎麼是受了瘴氣呢?母親說,這個人去遷墳,開棺時他沒躲開一下讓裏面的瘴氣散開後再撿遺骨,而是正沖著開棺的那股瘴氣,他現在這種耷耷的,像攝了魂一般的症狀,就是受了瘴氣的原因。我和病人聽了一起搖頭,覺得這又是中醫的一個謬論。
每當我埋頭在舊書堆中時,母親就把我拉到通風處、陽光下,說這些舊書有瘴氣。這時,我就更認同父親說中醫是巫醫的觀點了。
最近看報導,說當初開啟埃及法老墓穴的許多人受了病,曾被認為是遭到了法老詛咒。現經科學研究發現是墓穴中的一種特殊真菌對人的侵害。這使我不由得想到母親的瘴氣說。中醫雖然不知瘴氣中的真菌是什麼,但知道瘴氣能致病從而讓人躲避,這是很重要的。
面對有人嘲笑中醫是巫醫,我現在不以為然。小時候我把母親的許多認識或者當作人人皆知的常識,或者簡單地歸為中醫的“糟粕”,有時直接斥為愚昧,所以根本沒有在意。大半輩子活過來之後才發現,原來在中醫之外並沒有這種認識,母親站在中醫角度對精神的人和肉體的人的認識並不是落後的,有許多東西仍為當今科學解釋不了。
我承認找巫醫是一種無知的表現。我一個同事得癌症從北京做手術回來對我說,癌症病人有三分之一真是被嚇死的。我惋惜地想,如果這三分之一的人要是對癌症無知該有多好,要是有辦法能消除這三分之一人的恐懼該有多好,哪怕是用中醫或巫醫的手段也行。如果真知的作用是把人嚇死,那麼在性命和真知之間,我看還是保命為上,絕大多數的人並不是愛真理超過生命的。而有的人天生具有自我保護機制。我一個朋友一遇到緊急情況就昏死過去,把問題交給了我。另一個朋友對自己的重大錯誤失憶,不多不少,正正好好把錯誤那段全忘記。人的心理機制並不是讓人無限制地承受嚴酷的真實,這雖有悖科學精神,卻是大自然對人的慈悲。
(11)母親一臉茫然,她反復自言自語:“這糟粕不是糟粕?”
1 篇文章
• 第 1 頁 (共 1 頁)
1 篇文章
• 第 1 頁 (共 1 頁)
誰在線上
正在瀏覽這個版面的使用者:沒有註冊會員 和 2 位訪客